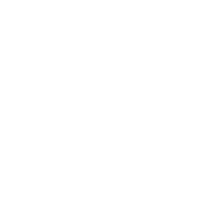□陈全洪
经常失眠的人对卧床怀有复杂情感:身心俱疲地想靠上去,而时睡时醒的状态又让人陷入不安的想象与痛苦中。酣眠已成为不能触及的记忆,一种当下难以企及的奢望。一个在床榻上常年辗转反侧的人,恐慌于时针在深夜的走动,千方百计地寻找适于入睡的时机与姿态。
殚精竭虑的物理时间与空间方位的调整,成了一溜架设在睡前忐忑与安然入眠之间的过渡缓坡,借此滑向夤夜的深寂与神安。作为一种理性的运动协调,翻来覆去的动作更多地渗入了心理安慰的成分,被视为抵达梦乡的必然途径并得到默然允许。
比如我会置万千信息于不顾,把手机关闭或调成飞行模式;唯有让它以主角身份退场,才能呼唤另一个主角上场、另一种场景轮现。
放下手机,开启另一种生活:放松内心,头颅后悬,挂于木质床沿。这个被我称为“挂脖”的动作,用以反抗白天长时间俯身带来的低头倦怠。即使时间稍长之后,颈肩袭来阵阵酸楚和痛感,它们也会被坦然接受,作为必定产生的附属产品或不可避免的副作用,忍受下来,期待着可能的正向结果。
悬挂动作持续,时针一格一格走过去,直到自认为累积到了一定质变的数值,才会停歇,整个身体复归日常状态。
“挂脖”之所以被我选为睡前的一门常规功课,就在于它的反日常、逆往常,能让自己从巨大的惯性轨道中,有幸跳脱,哪怕是短短的一两个时段,使自身在反常规的状态中,获得某种体位上的平衡并从中产生心理慰藉。睡前是相对放松的时段,侧卧、俯身或平躺等,都是较为自由的选项,或可让某种一定限度内可以承受的痛苦参与进来,使这个选项烙上自作自受的印痕。
当物理性方法不很奏效时,就得借助化学方法或者兼而用之。药物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。是否可以这样理解,失眠是人的大脑对白天生活场景、卧室的大小、方位、光线的明暗,以及眠床、被衾的色彩、质地等的过度反应,引起脑子神思亢奋以致无法入睡?药物减弱了大脑神经的敏感度,平息了燃起的兴奋性并渐至麻木——一个美好夜晚或许由此降临。
用在睡眠上,“麻木”是个褒义词。睡前思虑过多,而“麻木”将万千思绪拢为一束。很多时候,不是难为,而是不为。因此可说,克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,不易培养的自律能力。它的施行通常要借助外物,物理或化学方法,浇熄生生不息的散思碎想,让不为之事成行。
取最少量药物,舌下含服。垫好枕头,盖上薄衾,等着睡神的来临。不怕意念遄飞,不再辗转不安;即使有梦,那梦也是浅近清爽的,偶尔让人赏心悦目。
就像有一次,我来到村外的大桥旁,熟悉的桥堍位置,忽然闪现一片陌异风景,一道带着异域风情般的景致。如油画一般,一爿椭圆形湖泊围了一圈墨绿色植物,油彩发亮、高低错落,护着一泓心形的湖水。
我分不清,这是真实场景还是一幅画。
但你知道我内心的狂喜。我端起手机,忙不迭地拍了下来,生怕它划过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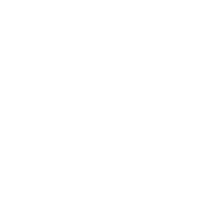
 放大
放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