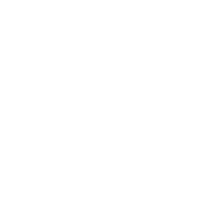□三川
一
无酒不成席,无饼不中秋。
前一句是民间俗语,耳熟能详;后一句虽为“潘说”,却并非“胡言”。因为中秋之于国人,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节日,把这个节日变成一只圆圆的月饼,把苦涩的日子变成甜蜜的念想,实乃古人之智慧。
月饼之大宗,一为广式,一为苏式。儿时所见所食,皆为苏式。用贾思勰那个时代的话来说,苏式月饼有“脆如凌雪”之口感。
女儿在深圳工作,中秋放假,是要回金华过节的。印象中,她小时候是吃过起酥的,却不一定记得住名称,我便故意吊她胃口:“家有起酥,喜欢吗?”
果不其然。她在微信里问我:“是吃的吗?”
起酥,个小、身薄、皮脆,乃苏式月饼之俗称。这一叫法,是否限于东阳、义乌、磐安一带,我没细究。但我知晓,八婺属吴语方言圈,“起”即启,意谓“开始、生发”,比如东阳方言中的“起屋”;“酥”是会意字,“酉”指“酒”,“禾”指“五谷”,“酉”“禾”相搭,特指“面粉加酒、糖等制成的一种松脆点心”。
打我记事起,起酥就是凭票供应,一人一票,一票限购2只,每只售价5分。当年,我们家7口人,中秋节前夕,爸爸要去一趟3公里外的供销社,添置一些节日用品。因为彼此相熟,营业员会主动将起酥分成两份。其中一份10只,用一方牛皮纸包起来,然后用细细的绳子捆扎,上头压一方小红纸点缀,上书“月饼”两字,这一份是用来孝敬外公外婆的。另外4只留给自家过节——中秋夜晚,掰碎一只起酥,兄弟姐妹分而食之,即便只得一小块,也足以让我们的童年变得甜蜜无比。如今想来,那饼是圆满的,恰似大而圆的月亮,明亮中带着一点点晕黄。
前两天,义乌文友潘爱娟“微”我说,义亭起酥开烘了,要来尝尝吗?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美味佳肴是要与人分享的。我爽快应承,还约请了公言、三余和钟炉,直奔义亭而去。
二
说起义亭起酥,王义民是一位绕不开的匠人。
聊天间隙,煮水壶发出咕嘟咕嘟之声。王义民给我们斟上茶水,便去到隔壁车间,取来10只黄灿灿的起酥做茶点——“烫!烫!烫!”刚放下托盘,他连说3个“烫”字,提醒我们过会儿再吃。
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。”起酥脆皮,一层又一层,层层薄如蝉翼。想当年,物流不畅,加之烘焙工艺等原因,等中秋入嘴,起酥表层早已结壳。但在物质匮乏年月,还是觉得无般不好。吃的时候,总是一只手撮起,另一只手承着,够到唇边,轻轻咬上一口,满嘴油香。只是,即便如此轻拿轻咬,还是有碎屑不断落入掌心。饼刚吃完,便伸出舌头舔掌心。
金华人都有体会,平日吃酥饼,现烤的好吃不止一点点。起酥温热,我们还像小时那样,撮起一只。所不同的是,另一只承着的手中多了一张餐巾纸。轻轻咬去,有浓稠的芝麻馅粘在唇间;掉落的皮面是软的,不很松脆,但一触即碎。至于口感,“不觉甚甜,而香松柔腻,迥异寻常”。潘爱娟血糖偏高,本应忌口,却见她用矿泉水吞了一颗药丸,也忍不住吃了一只。
“三分饼,七分炉”,乃业内行话,意谓月饼好吃与否,三分靠和面、擀面、包馅功夫,七分靠烘焙。
在发面车间,但见两名女工将2袋各25公斤的面粉倒在一张长长的条桌上,用勺子整出一个圆形凹槽,倒进一筒2.5公斤浓稠猪油,慢慢添水,将其搓揉成一团团油酥面。取一根擀面杖,将揉捏好的油酥面擀成一张长方形的面皮,对半切开,分别从侧面“内卷”,再把卷好的面皮复擀成长条。
据说,这道“起酥”工艺最是复杂,也至关重要——脆皮的层次,全靠那“内卷”。内卷越频,层次越分明。莫非,“起酥”之名,即源于此?
油面“起”好,摘成一个个小小的饼坯,依次端给包馅师傅。馅料是起酥之魂。传统馅料,无非是白糖、芝麻、核桃、百果、豆沙、枣泥等。馅料不同,口味上会有差别,但在饥不择食年代,哪样都觉得好吃。及至衣食渐丰,挑肥拣瘦也是必然。于是乎,低脂少糖的红豆、椒盐、火腿、香辣牛肉、香芋和三馅(蛋黄、肉松、巧克力)等,又迎合了顾客胃口。
如果有人被“水晶”所惑,来上一只的话,恐怕会大失所望。所谓“水晶”,晶亮透明,其中之一就是肥肉丁。另外不可或缺的,就是小颗粒冰糖。20世纪70年代,水晶月饼是饼中翘楚,那肥肉丁混杂着冰糖粒,以及其他甜蜜馅料,还有酥皮,在嘴里引发的就是一场诡异的咀嚼风暴,猪油搞不好会从嘴边流出来。这对成日毫无油水的旧年百姓来说,无疑是一次满足“油大”追求的机会。却不想,风水轮流转,在《调鼎集》中有记载的水晶月饼,现如今连个名儿也不提了。听王义民解释,成亦肥肉败亦肥肉,随着肥肉形象越来越差,水晶月饼也就跟着走了下坡路,早在10年前就不生产了。
三
月饼之谓月饼,据说与朱元璋起事有关。如此说来,馅里有肉的月饼恐怕都无资格被叫“月饼”吧?因为“食菜事魔”的明教,月饼肯定是素的。不过,这么一想,倒也别有一番意趣——各种馅料、不同皮面的饼,是怎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都出现在八月十五,然后被叫月饼的呢?时至今日,不管作何种假设,就月饼功效而言,“摆”之仪式显然要比“吃”更重要了。
说来也怪,苏式月饼较之于广式,保质期要短得多。不抓紧吃,在秋老虎还徘徊不去的中秋节前后,很快就会“哈”掉。
从义亭返回,起酥是伴手礼,摆放在餐桌一角。因为临近保质期,牛皮纸已被油渍浸透。稍稍靠近,即可闻到那悠长的甜蜜和诱人的芳香。
那天女儿从深圳归来,见着起酥,冷不丁地冒出一句:这不就是小时候吃过的土月饼吗?
平心而论,土月饼灰头土脸的,样貌远没有广式月饼好看。就像义亭起酥,里外都是简装,饼面没有凸浮纹饰,一枚红红的印章便是其唯一标识,每只售价还不到两块钱。但就是这么普通的时令饼食,让我们想起了甜蜜的童年,以及金钱之外的明月清风:“中秋夜月抬眼望,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夜佳期有机趣,月圆月缺不费钱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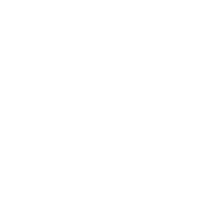
 放大
放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