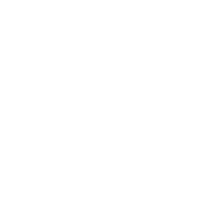□许旭锋
暑假快结束时,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参加工作的第一站——八达。
一
从东阳市区出发,开车45分钟左右就来到了东阳江镇横锦村。汽车驶上横锦水库大坝,映入眼帘的是碧波荡漾的水面,源源不断地为东阳人民提供优质的饮用水。
受地形、气候因素影响,昔日的东阳江旱涝频繁,甚至到了三年两灾的地步,东阳江也因此被称为“烂肚肠”。1958年,当时东阳县委、县政府痛下决心在上游修建水库来整治东阳江。这年秋天,全县组织大批干部,抽调几万民工参与建设。同年9月26日,横锦水库正式开工建设。想当年,红旗漫卷插遍工地,劳动号子响彻云天,构成了一幅战天斗地的宏大图景。如今的横锦水库,大坝高57.5米、长295米,控制流域面积378平方公里,最大库容2.74亿立方米,是一座以灌溉、防洪为主,结合供水、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,对东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泽润八方,饮水思源。为支持横锦水库建设,库区百姓“舍小家、为大家”,8900多人背井离乡,异地安置。他们克服生产生活中的困难,在异乡艰苦奋斗、重建家园。他们与水库建设者一样,都是时代的英雄!
沿着水库蜿蜒行驶。“爸爸,转了这么多弯,还有多久到八达呀?”孩子问道。这个情境与我22年前第一次到八达报到时一样。当时我坐着公交车,也满怀好奇地向身边的乘客问相似的话。从水库大坝开始,一路山重水复、起起伏伏,很期盼下一个转弯处就是目的地。
事实上,从大坝开始行车至少还有40分钟才能到八达。水库移民后,库区的村庄规模都不大,沿途经过的村庄都只有零星的房子。而八达正好处在山峡间的一块盆地,空间较为开阔,适合聚居,因而成了库区最大的村庄。
汽车快到东门村时,向左拐过东门桥,再翻过一座大山,从山门前村一直往东,经过尚舒村,眼前豁然开朗,但见群山环抱之间屋舍俨然、阡陌纵横、双溪汇流,八达村到了。
二
曾经的八达乡政府就在村西口,门楼朝南挨着马路,两扇大门孤独地守候着,已经锈迹斑斑。门楼内建筑呈回字形,西边是一幢三层砖混结构的房子,工作人员办公和住宿都在这儿;东边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,20多年前就已破旧,主要用做食堂,现已倒塌。当年,若西边较新的房子宿舍不够,像我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男同志,就要先住在这幢楼的二楼过渡。这儿的楼梯、楼板和扶手都是木质的,比较陈旧,踩上楼梯,木板就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夜晚的八达十分安静,适合灯下拾零,看看书或者写点东西,经常能听到老鼠在地板上来回跑动的声音,一开始心里有些害怕,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。山区工作虽然清苦,却让人难忘。
乡政府的旁边有两条溪,一条是秀溪,一条是镜溪,在八达村汇合后流入横锦水库。两溪交汇处有座桥,是东至磐安西通东阳的必经之处。八达桥头也是该村最热闹的地方,特别是在夏天,夜幕降临,人们就搬出竹椅、摇着蒲扇,靠在桥栏杆上乘凉。晚间的山风带着溪水的凉气,吹在身上比空调风舒服。迎着凉风习习、听着流水潺潺,老人家喝茶闲聊,孩子们追逐嬉戏,山村的夜晚和谐而安宁。
当年在乡政府食堂烧饭的飞跃阿姨就住在桥边,我决定去看看她。推开门,飞跃阿姨正在做手工活。“飞跃阿姨!”我喊了一声。阿姨抬头望着我,愣了一会儿,并没有认出我来。毕竟20多年没见了,她的头发已经花白,背也有点驼,但气色还不错。我自报家门,她马上起身,脸上堆满了笑容,一边给我让座,一边拉着我儿子的手。“认不出了,认不出了,儿子都这么大了,时间过得真快呀!”阿姨忙活着给我们泡茶水、递饮料,这么多年了,她待人的热情劲一点儿没有变。
思绪带着我回到22年前。当年的同事多为30岁不到的年轻人,八达地处偏远山区,大家都住宿舍,一周回家一趟,一日三餐都由阿姨负责。记得我参加工作第一天,端着饭盒走进厨房蒸饭时,阿姨和蔼地对我说:“是新分配的大学生吧?年轻人饭要吃饱。”乡政府的早餐多为面条,年长的同事起得早,而年轻人习惯懒床,吃早饭的时间点七零八落,为了不让面条糊了,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分次给大家下面条,并一个劲地催“多盛点、多盛点”,就怕年轻人饿肚子。甚至有时,她已把厨房收拾好了,起得晚的同事来到厨房吃早饭,她还是乐意为其开小灶,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干。阿姨烧的红烧肉肥而不腻,是当时的招牌菜。当然,春笋咸菜炖豆腐、姜丝溪鱼干、丝瓜豆腐、炒南瓜、毛菜芋艿等,现在想起来也都是舌尖上的美味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她一直工作到食堂停办。
当我起身准备告别时,阿姨极力挽留我们吃了中饭再走。我婉谢了,生怕再尝到熟悉的味道时,触动内心不能自已。
三
离开八达,我们继续开车,前往我曾联村过的学陶村。八达到学陶的公路已铺上沥青,十分平整。沿镜溪溯源而上,两侧树木成荫,绿意葱茏。
首先路过王毛弄村,这个原本破旧的小村落,如今已完全改变模样。路边建起了许多楼房,门前便是绿水青山,清澈见底的溪流中石斑鱼成群结队。纸铺村在王毛弄村上游,也是沿溪而建。溪上的纸铺大桥巍峨壮观,桥头建有观景亭。站在观景亭里,山峦倒映,碧树蓝天,白鹭翔集,锦鳞游泳,美景尽收眼底。
离开纸铺村,一路往东驶,就进入了龙潭大峡谷。八达水库大坝就建于此。大坝高40余米,像一个竖立的鳖壳,拱弧向里,拦截着碧绿的库水。大坝两端,高山耸峙,危峰兀立,青山倒映在绿水中,与四周的自然景色构成一幅美妙的山水画卷。因为建了这个水库,原本通往学陶的公路在这里突变陡峭,不得不从高于大坝的半山腰通过。水库大坝往里3公里,就到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学陶村。
学陶村地处海拔700米的峡谷间。见证村庄悠久历史的,除了绵延青山和清澈平板溪外,还有守候村口的千年红豆杉、岩岫间的古榧树以及漫山的云雾茶。村口这棵红豆杉已经有1000多年树龄,高20余米,胸围6.5米,需要4个大人才能合抱。针叶青翠高雅、树形挺拔坚韧,树冠遮蔽半亩山地,在金华称得上红豆杉王。学陶村有256棵300年以上树龄的古榧树,榧果以形尖壳薄黑膜无涩异于常榧,形似蜂儿、味甘如蜜,食之如酥。《本草纲目》载:榧子又名赤果、玉榧、玉山果。学陶毗邻玉山,学陶香榧古称玉山果、蜂儿榧。苏东坡以“彼美玉山果,粲为金盘实”盛赞玉山果。学陶茶叶,品质上佳。记得在联村时,我来到炒茶能手徐万妹家,她热情地泡上一杯刚出锅的新茶,热气腾腾,清香四溢。杯中茶叶颜色翠绿,汤色清澈明亮,叶底嫩匀成朵,抿上一口,滋味鲜爽甘醇。提起学陶茶叶,村里人都很自豪,因为茶叶好,当年玉山古茶场的茶市都要等学陶茶到位后才开市。如今,学陶已发展了500多亩香榧和430多亩高山茶叶基地,春采茶叶秋摘榧,学陶人走上了致富路。
学陶村老支书徐仁德是村民致富的领头人。1997年,他带头学习香榧授粉技术,让200多棵百年古榧重焕生机、硕果累累;建立榧苗圃,推广育苗嫁接技术,使香榧得以规模化种植;成立香榧专业合作社,从事香榧炒制、包装和销售,提高了附加值。徐仁德在担任村干部期间,干事利落、勤勤恳恳、一心为民,深受群众好评。2003年10月,我到学陶村担任联村干部时,徐仁德还担任村支书。初到学陶,涉世不深、没有联村经验加上语言差异,让我一度内心彷徨。此时,徐仁德给予了我热情的欢迎和真心的帮助,让我很快进入角色。我叫他“仁德书记”,他叫我“许秘书”,我们配合得很默契。其间,大家一起努力成立香榧专业合作社、注册茶叶商标、实施康庄工程……一件件实事落地,颇有成就感。一年多相处,让我深切感受到山区干部的热情、朴实和坚韧。2004年12月,我离开八达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后,与仁德书记还常有联系。不幸的是,2016年白露时节,仁德书记在采摘香榧时不慎从树上摔下来导致瘫痪,从此只能轮椅相伴。
2017年春节,我曾回到学陶看望过仁德书记,如今状况如何呢?推开他家门,看到他坐着轮椅,头趴在前面八仙桌上正在休息。“仁德书记”,听见我的叫唤,他抬起头望着我,顿了顿,眼前一亮,马上应了句“许秘书”。此时,徐师母也从厨房走到客厅,赶紧给我们让座泡茶。我坐在仁德书记身旁,询问身体状况和村里的变化。76岁的仁德书记头发稀疏,原本黝黑的肤色因常年居家有些发白,尽管腿脚不便,但精神良好、思维清晰。谈及孙女今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学,他的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。徐师母也一刻没有闲着,在厨房里为我们准备点心,一定要让我们吃了再走。盛情难却,恰好我也可陪着仁德书记多聊聊天。
吃完点心,我起身向告别。此时,徐师母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包,硬要塞给我的孩子。“拿着,买点好吃的,快长快大!”推辞不过,我只好让孩子收下。我们刚上车,徐师母又急匆匆地从家里出来,手里拿着两包择子粉。“自家的择子粉,没有沥好,颜色有点黑,不影响口感的。”说着就塞进我的车窗。我向徐师母挥手告别,不舍地离开了学陶。
时光飞逝,又见八达。难忘的是这里的绿水青山,更有淳朴善良的人们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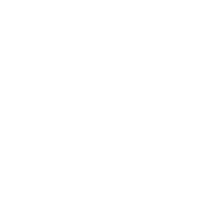
 放大
放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