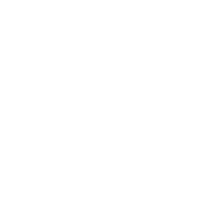近千年过去,曾经的“城”已然不存,横亘绵长的溪塍也已经失却昔日模样,就连它拱卫过的义塾也已被岁月无情抹去,唯有洗马塘自然村内怡和堂的“两朝义学”牌匾和宗谱里的记载,见证着一段历经四世三朝而百折不挠的坚守。
蒋沐何以会创办横城义塾?根据家谱记载,此事和其父亲蒋元广有关。蒋元广善于理财,为人侠义,虽以捐官方式获授迪功郎从九品虚职,但他天性恬淡,以教育子孙为要事,意欲办学并免费招纳弟子入学,惠及一乡子弟,但此事未付诸实施即去世。富于才干、倜傥尚义的蒋沐决定继承父亲遗志,于宋景定元年(1260)建造义塾。蒋沐还邀请当世理学大家、淳安籍状元方逢辰主师席,方不仅欣然应允,还为义塾题字“开塾宏教”。
次年春,方逢辰扁舟泛雪而至,为横城义塾制定了塾规,创新教法,“每旬九日读圣贤书,讲明穷理,正心修身;一日学习科举业”。方逢辰将前者视为“本”,而视后者为“末”,认为治人之道远比科举之业更为重要,以此教学之法可达本末兼顾之效。在此前提下,每旬还要举行课试,上中旬考本经,下旬论策,每次试10人,取前三名给予奖励;每月还有模拟科举考试的“拟试”,前三十名不仅奖励钱帛书籍,还效仿唐代进士“雁塔题名”之举,获“砻石题名”之誉,仅3年题名者就达685人。
在视科举业为教学核心的宋代,方逢辰的这一规定可谓“拨乱反正”之举。不仅如此,方逢辰还借鉴白鹿书院学规,梳理出朱熹所录先贤格言,明示于学斋、公堂等;又仿蓝田吕氏乡约,围绕“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、礼俗相交、患难相救”,在东西厢房明示修身处事之道,引导学生成为谦谦君子。这些内容都被刻于石板之上,置于屋内。
横城义塾对于生源不作限制,但制定了严格的筛选程序:学子刚入学时为“陪供生”,通过德业考试后转为“行供生”即正式学生,可以享受免费食宿,蒋沐为此每年划拨一万贯田租作为义塾运营经费。因此,横城义塾虽为一乡之塾,但不远千里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,柳贯、陈一中、吕应焱、吴龙朋等大儒也先后前来执教,蒋氏子孙由此广闻博见,才学兼优。
宋咸淳六年(1270),蒋沐为奸相贾似道所害,贬至岭南,居庐陵,义塾遂废。元至元十五年(1278)蒋沐归乡后,在祖居3里开外的南溪之上建别业以安置幼子蒋吉相,又将义塾残构迁至溪东建造城南精舍,以图恢复义塾旧观,其址即在原南溪啤酒厂一带。元至元二十一年(1284),城南精舍竣工,蒋沐却遽然去世。年仅11岁的蒋吉相在母亲郭氏与兄长扶持下,支撑起城南精舍事务。但他在成年后赴京城供职,后担任谷城尉,城南精舍又废。蒋吉相去世后,其长子蒋元于元至治二年(1322)在城南精舍南面的黄金坞重建义塾。黄金坞,今属安儒村,在安儒村北面、南溪村东面。
蒋元为元代大儒许谦的高足,他自主师席,重聘方逢辰任教,宋濂、王袆、高明等名士皆慕名前来求学,黄溍、陈樵、胡助等往来其间,门人弟子填其室。为追念祖父与父亲的办学功绩,他多方收集镌刻义塾学规的石板,在义塾附近的东冈建怀远亭,将石板嵌于墙内。
元至正四年(1344),蒋元去世,其长子蒋伯康奋然继任塾主。此前,因义塾被大风所毁,蒋元将其迁回洗马塘。蒋伯康在此基础上扩大规模,授教生徒数以千计,成材者甚众。此期的横城义塾因历元、明两朝,声名卓著,明代开国元勋刘基为其题词“两朝义学”。
义塾的规模到底有多大?蒋德鱼幼年时曾听老人家言,东起洗马塘边的双喜桥,西至上朱村外,北起义乌到东阳的官道,往南至凤仪自然村的望儿桥一带,都属于义塾范围。相传,学子前来义塾求学,过了望儿桥就要换上统一的服装,类似今天的换校服仪式。“很小的时候我们还知道义塾有口方塘,蒋伯康用石板铺底,称为石板塘,塘的前后筑有水阁。”后来蒋伯康又在此塘周边辟园圃,植花木,建以亭台楼阁,统称龙谷精舍,又名横城别墅。根据家谱记载,这些亭台包括净香亭、春晖堂、安乐窝、爱日轩、友怡堂,宋濂、黄溍、陈樵等当世大儒均为之作记、赋诗、献序。宋濂不仅曾在义塾求学,后来还与蒋伯康家族有姻亲之谊,往来密切,其所作《东阳马生序》中所言“当余之从师也,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,穷尽烈风,大雪深数尺”,就是对他赴横城义塾求学场景的写照。
但这段关系也为蒋氏家族带来没顶之灾——明洪武十四年(1381),因宋濂的长孙宋慎受胡惟庸案牵连,蒋氏族人恐受株连,将谱牒分为“晋陵”“弋阳”两郡,蒋沐一支称为“晋陵”,此即蒋沐后人改名为“晋陵洗马塘蒋氏”之缘由。随着风声日紧,洗马塘蒋氏族亲弃产外逃,义塾就此停办。两年后,蒋伯康谢世。正统七年(1442)八月,义塾遭受洪灾,房舍湮没,历经四世三朝的横城义塾就此谢幕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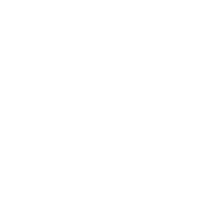
 放大
放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