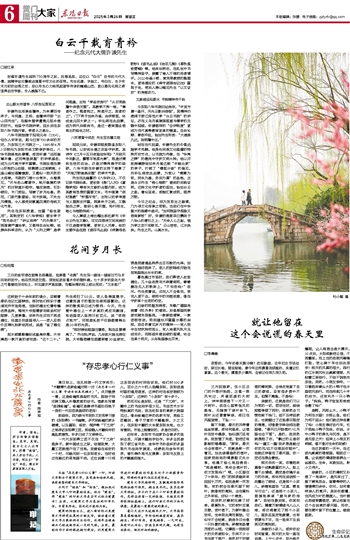这段始于十余年前的缘分,总随着春讯在记忆里鲜活。那时他们相识于澧浦花卉市场角落,当别的摊主忙着夸耀名贵品种,唯有大爷指着茶花细说何时嫁接、几度寒暑。后来先生买花不再逛摊位,径直去田垄里寻人——老人总把价压得比别家低两成,说是“省了摊位费”。
泥水顺着棚檐织成晶亮帘幕。大爷捧起一株尺高的茶花苗:“这个二十。”先生却扫了50元。老人急得直摆手,沾着泥星子的银发在细雨里颤动。这样的默契早已成为惯例:今天,先生看中摊位上一米多高的虎皮花鹤翎,电话里老人坚持只收百元,说“老桩占地方”,可那盘虬枝干任谁都看得出是20年的光阴。
“那时候他眼里汪着愁,现在总算清亮了。”先生轻声说。几年前大娘生病住院,大爷整宿蹲在苗圃照看30盆茶花,愣是把普通品种养出玉石般的光泽。如今大娘好起来了,老人的胶鞋却开始在泥地里拖出长长的痕。
暮色漫过市场时,我们帮老人收拾摊位。几十盆名贵花木淋着细雨,静静躺在无人的铁架上。“不怕丢吗?”我问。先生笑着说,买花人不会偷花,卖花人更不会。细雨中的花苞低垂,像在守护某个古老的约定。
归途的雨越发绵密,车载广播里流淌着《牡丹亭》的唱词。后备厢里两株茶花随车身摇晃,一株新苗青翠,一株老桩苍劲。雨刮器划开重重水幕的刹那,我忽然看见岁月的模样——有人把半生悲欢种进泥土,有人将春风秋月兑成花价,而那些未曾说破的温情,终会在某个雨天,从年轮里渗出芬芳。
□包钰莲
三月的金华浸在烟青色雨幕里,我跟着“花痴”先生深一脚浅一脚踩过竹马乡田地的泥泞。他忽然拐进岔路,领我钻进挂着水帘的塑料棚。七十多岁的卖花大爷正弓着腰给茶花松土,听见脚步声直起腰,沟壑纵横的脸上绽出笑纹:“又来啦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