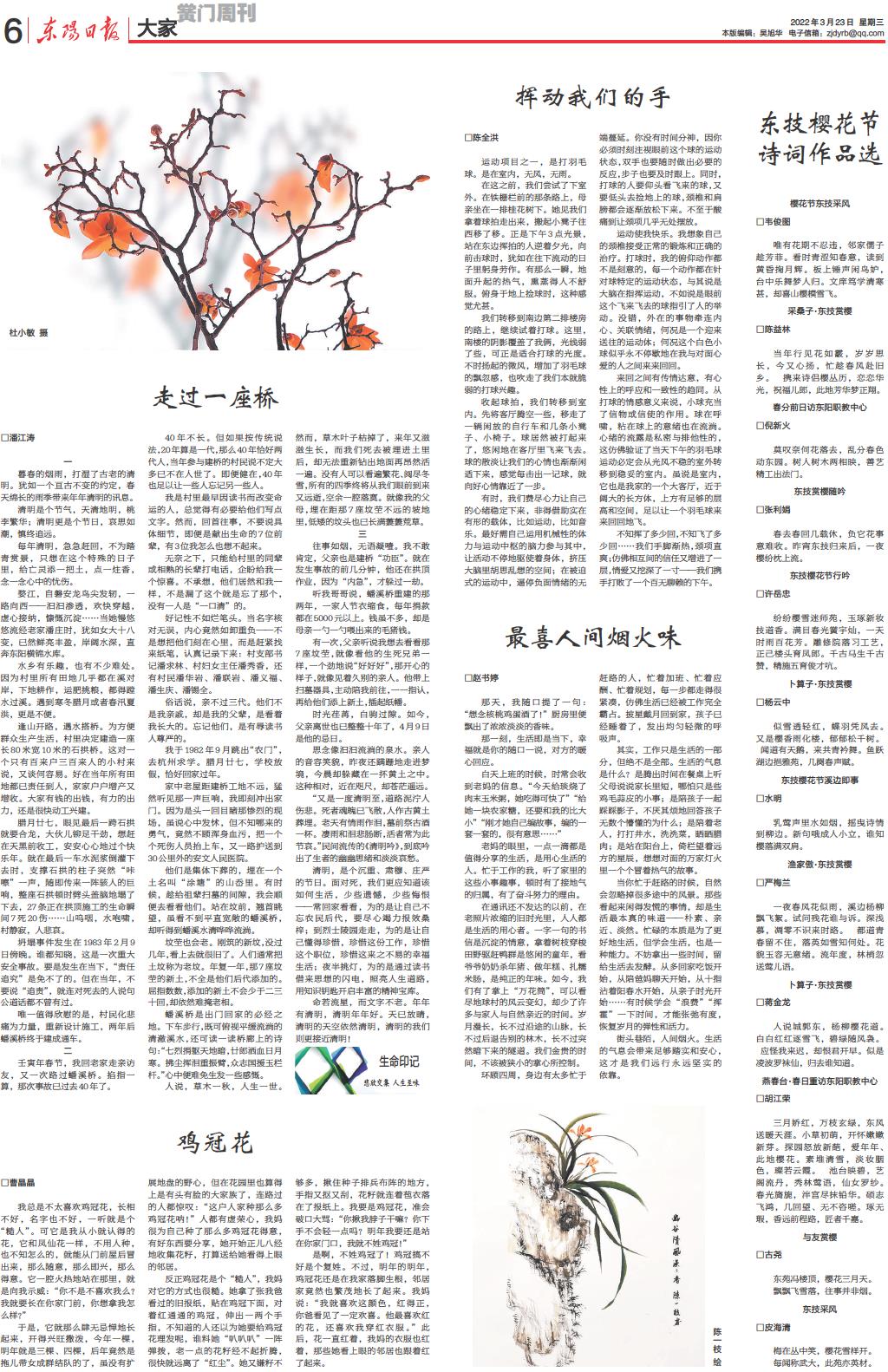□潘江涛
一
暮春的烟雨,打湿了古老的清明。犹如一个亘古不变的约定,春天绵长的雨季带来年年清明的讯息。
清明是个节气,天清地明,桃李繁华;清明更是个节日,哀思如潮,慎终追远。
每年清明,急急赶回,不为踏青赏景,只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给亡灵添一把土,点一炷香,念一念心中的忧伤。
婺江,自磐安龙鸟尖发轫,一路向西——汩汩渗透,欢快穿越,虚心接纳,慷慨沉淀……当她慢悠悠流经老家潘庄时,犹如女大十八变,已然鲜亮丰盈,岸阔水深,直奔东阳横锦水库。
水乡有乐趣,也有不少难处。因为村里所有田地几乎都在溪对岸,下地耕作,运肥挑粮,都得蹚水过溪。遇到寒冬腊月或者春汛夏洪,更是不便。
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。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,村里决定建造一座长80米宽10米的石拱桥。这对一个只有百来户三百来人的小村来说,又谈何容易。好在当年所有田地都已责任到人,家家户户增产又增收。大家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还是很快动工兴建。
腊月廿七,眼见最后一跨石拱就要合龙,大伙儿铆足干劲,想赶在天黑前收工,安安心心地过个快乐年。就在最后一车水泥浆倒灌下去时,支撑石拱的柱子突然“咔嚓”一声,随即传来一阵骇人的巨响,整座石拱顿时劈头盖脑地塌了下去,27条正在拱顶施工的生命瞬间7死20伤……山呜咽,水咆啸,村静寂,人悲哀。
坍塌事件发生在1983年2月9日傍晚。谁都知晓,这是一次重大安全事故。要是发生在当下,“责任追究”是免不了的。但在当年,不要说“追责”,就连对死去的人说句公道话都不曾有过。
唯一值得欣慰的是,村民化悲痛为力量,重新设计施工,两年后蟠溪桥终于建成通车。
二
壬寅年春节,我回老家走亲访友,又一次路过蟠溪桥。掐指一算,那次事故已过去40年了。
40年不长。但如果按传统说法,20年算是一代,那么40年恰好两代人,当年参与建桥的村民说不定大多已不在人世了。即便健在,40年也足以让一些人忘记另一些人。
我是村里最早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人,总觉得有必要给他们写点文字。然而,回首往事,不要说具体细节,即便是献出生命的7位前辈,有3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无奈之下,只能给村里的同辈或相熟的长辈打电话,企盼给我一个惊喜。不承想,他们居然和我一样,不是漏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,没有一人是“一口清”的。
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当名字核对无误,内心竟然如卸重负——不是想把他们刻在心里,而是赶紧找来纸笔,认真记录下来:村支部书记潘求林、村妇女主任潘秀香,还有村民潘华岩、潘联岩、潘义福、潘生庆、潘锡全。
俗话说,亲不过三代。他们不是我亲戚,却是我的父辈,是看着我长大的。忘记他们,是有辱读书人尊严的。
我于1982年9月跳出“农门”,去杭州求学。腊月廿七,学校放假,恰好回家过年。
家中老屋距建桥工地不远,猛然听见那一声巨响,我即刻冲出家门。因为是头一回目睹那惨烈的现场,虽说心中发怵,但不知哪来的勇气,竟然不顾浑身血污,把一个个死伤人员抬上车,又一路护送到30公里外的安文人民医院。
他们是集体下葬的,埋在一个土名叫“涂塘”的山岙里。有时候,趁给祖辈扫墓的间隙,我会顺便去看看他们。站在坟前,翘首眺望,虽看不到平直宽敞的蟠溪桥,却听得到蟠溪水清哗哗流淌。
坟茔也会老。刚筑的新坟,没过几年,看上去就很旧了。人们通常把土坟称为老坟。年复一年,那7座坟茔的新土,不全是他们后代添加的。屈指数数,添加的新土不会少于二三十回,却依然难掩老相。
蟠溪桥是出门回家的必经之地。下车步行,既可俯视平缓流淌的清澈溪水,还可读一读桥廊上的诗句:“七烈捐躯天地暗,廿郎洒血日月寒。拂尘挥泪重振臂,众志国援玉栏杆。”心中便难免生发一些感慨。
人说,草木一秋,人生一世。然而,草木叶子枯掉了,来年又滋滋生长,而我们死去被埋进土里后,却无法重新钻出地面再昂然活一遍。没有人可以看遍繁花、阅尽冬雪,所有的四季终将从我们眼前到来又远逝,空余一腔落寞。就像我的父母,埋在距那7座坟茔不远的坡地里,低矮的坟头也已长满萋萋荒草。
三
往事如烟,无语凝噎。我不敢肯定,父亲也是建桥“功臣”。就在发生事故的前几分钟,他还在拱顶作业,因为“内急”,才躲过一劫。
听我哥哥说,蟠溪桥重建的那两年,一家人节衣缩食,每年捐款都在5000元以上。钱虽不多,却是母亲一勺一勺喂出来的毛猪钱。
有一次,父亲听说我想去看看那7座坟茔,就像看他的生死兄弟一样,一个劲地说“好好好”,那开心的样子,就像见着久别的亲人。他带上扫墓器具,主动陪我前往,一一指认,再给他们添上新土,插起纸幡。
时光荏苒,白驹过隙。如今,父亲离世也已整整十年了,4月9日是他的忌日。
思念像汩汩流淌的泉水。亲人的音容笑貌,昨夜还蹒跚地走进梦境,今晨却躲藏在一抔黄土之中。这种相对,近在咫尺,却苍茫遥远。
“又是一度清明至,道路泥泞人伤悲。死者魂魄已飞散,人作古黄土葬埋。老天有情雨作泪,墓前祭古酒一杯。凄雨和泪悲肠断,活者常为此节哀。”民间流传的《清明吟》,到底吟出了生者的幽幽思绪和淡淡哀愁。
清明,是个沉重、肃穆、庄严的节日。面对死,我们更应知道该如何生活,少些遗憾,少些悔恨——常回家看看,为的是让自己不忘农民后代,要尽心竭力报效桑梓;到烈士陵园走走,为的是让自己懂得珍惜,珍惜这份工作,珍惜这个职位,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;夜半挑灯,为的是通过读书借来思想的闪电,照亮人生道路,用知识钥匙开启丰富的精神宝库。
命若流星,而文字不老。年年有清明,清明年年好。天已放晴,清明的天空依然清明,清明的我们则更接近清明!